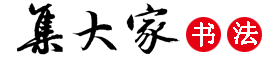来自 诗草堂 公众号
时代骑手
——在黑马上缔造现代诗歌的命运共同体
马小盐
马小盐,女,七十年生人,小说作者,文化批评家。
为何从眼中射出黑色的光芒?
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。
——布罗茨基《黑马》
起源与目的
现代性一词,对很多诗人来说,似乎具有天然的正确性。尤其是口语诗这一领域,每每与大众发生冲突,口语诗群体为自身辩护的最佳佑词便是:这是现代诗歌,你们不懂。在这里,作为修饰词的“现代”,成了各类面目可疑之人的庇护所。一旦躲避在“现代”一词的冠冕下,各路徘徊在语言之门外的文学痴汉,即使作品糟糕透顶,亦可获得合法的赦免权。事实上,这种争辩,隐含着一种逻辑,一种租借自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文学进化论逻辑:因为是现代的,所以一定是先进的、先锋的。现代诗歌亦然。
但现代诗歌真如现代科技一样,比起古典诗歌,更为先进与文明吗?显然不是。现代性这位多产的母亲,她的婴孩众多。有的一路成长,有的半路夭折,有的已接近畸形的怪胎,譬如现代艺术。在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看来,现代艺术大多是堆积进博物馆的毫无意义的垃圾。鲍德里亚的观点,我有赞同之处,亦有反对之处。时代产生垃圾,亦产生珍宝,艺术史不过是从垃圾堆上选取珍宝的过程。任何时代,艺术的垃圾可能远远多于精品。后世留存下来的艺术,只会是金字塔塔尖的作品,而非全部。现代诗亦然。诗的好坏,与诗本身的语言、意象、韵律、生命力有关,与现代不现代没有必然的关联。所有的古典诗,对书写和当时阅读他们的人来说,都是当代诗。古典,只是后来者的一个分类罢了。古典诗,有好诗,也有坏诗。现代诗,当然也有好诗与坏诗。只是因时间之筛的筛选,古典诗中的好诗如今仍旧能够映入我们的眼帘,坏诗却已经湮灭于岁月。我们之所以无法分辨出同时代诗歌之好坏,那是因为我们仍旧身处时代之环的一链,未能窥破时间之筛最终的谜面。
提起现代诗歌,我们有必要厘清这个词汇的起源。现代诗歌起源于何处?众所周知,中国的现代诗起源于“五四”白话文运动。而“五四”白话文运动,则源于现代文明与这片古老土地的正面相逢。当这艘朽坏老腐的巨船,与现代文明迎面撞击,其结果令大多数中国知识人瞠目结舌:我们并非万邦来朝,屹立于世界的中央,反而远远落后于世界诸民族。这简单而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感,引发了当时知识界普遍的危机意识,文化改良与民众启蒙成了当务之急。而文言文的教条繁冗,早已与现代社会无法调和,并成了启蒙民众、提高素质,最终与民众交流并达成共识的障碍,于是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开始了。滥觞于白话文运动的中国现代诗,就此走上了它的蹒跚探索之路。
众所周知,中国现代诗的原点之作,《蝴蝶》一诗,就是白话文运动的发起人之一——胡适的作品。这首诗歌,虽然形式尚未摆脱旧诗(五言律诗)的传统,语言却浅显直白,简单易懂。它稚嫩、天真、口语化十足,笨拙得就像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。胡适自己声称,他的新诗“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……虽然一年放大一年,年年的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。”胡适之所以如此自省,是因他觉得自己的诗歌仍旧摆脱不了传统格律的束缚。然而,胡适诗作真正的弊端并非于此。真正的原因在于,胡适匮乏作为诗人的才华。他缺少诗人对词语、意象、语音的基本敏感,更缺少诗人的天赋与性灵。他仅仅是一个醉心于文化改良的知识人,而非缪斯选中的情人。反而是鲁迅的几首调侃性诗歌,诸如《我的失恋》《梦》《人与时》,从语言到意象,比胡适的诗歌,更显露出被缪斯女神吻过的印痕。
如果说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传道者,鲁迅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先知。传道者与先知的区别在于,传道者传播他所看、所知、所倡导的一切。在道与民众之间,他是桥梁。先知则在黑夜里呐喊的同时,返回传统,反思传统,并预言未来。在道与民众之间,他既是阐释者又是原创的祭司。比起传道者,先知更有灵性,也与缪斯更为亲近。这也是鲁迅的诗歌,为何优于胡适的缘故之一。但无论胡适还是鲁迅的白话诗歌,他们的目的,皆非抒发一己之情、一己之感,他们的本意,原本便在于开风气之先,与民众一起,创造一个新世界,生成一种新文化,缔造一个民族复兴的文化共同体。
失踪的他者
厘清了中国现代诗歌的起源与目的,我们便会发觉,如今中国的现代诗歌,早已错失了当初的目标,反而迷失在由各种思潮所构筑的米诺斯迷宫之中,这迷宫里的怪兽,不是牛头人身怪物,而是诗人们那个过度膨胀的“我”。诗人与读者之间,往往处于对立的两极:诗人自诩高级文化的代言人,拒绝给民众写诗,民众亦不理解诗人所谓的现代诗歌。民众与现代诗歌的隔阂,一如博尔赫斯与他恋人的隔阂:“在我的爱人与我之间,必将竖起/三百个长夜如三百道高墙。”在我们这里,有时甚至会演变为:“在我的读者与诗歌之间,必将竖起/三百道高墙如三百种痛骂。”
为何出现如此难堪的二元对立局面呢?这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。八十年代改革开放,再度敞开的国门,迎纳了欧美四、五十年间集聚如浪的文化思潮。存在主义、结构主义、女权主义、后现代等等,一浪接一浪的与马克思主义杂交的知识浪潮,在极短的时间内,不问禾稗,蜂拥而入,击打着这片荒芜而饥渴的土地。大部分中国知识人,被这些浪潮吸引并捕获。诗人,这语言的祭司,这种族里最为敏感的人群,首当其冲地成为接纳新思潮的最佳器皿。
熟知哲学思想的人知道,从存在主义,到后现代主义,皆倡导个人主义与个性解放。诗人,原本便是一个容易自傲的群体,在这些零散思潮只言片语的影响下,更容易成为一个膨胀的唯我论者。他们把放浪形骸当做灵感的食粮,把唐璜式轻薄当做罗曼蒂克的自我,把潮流熏陶下的戏剧性“假我”当做了“真我”——在扮演诗人与真实诗人之间,他们自己,亦分不清哪一个是自己的面具,哪一个又是真正的“我”。这导致大量的中国现代诗中,自我与萦绕着自我而催生的假面齐飞,却罕见他者的在场。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曾将现代社会的此种现象,归罪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对他者的过度同化。这种将他者还原为同者(将他者同化为我,我的思想,或者我的财产)倾向,最终会将他者变成一种自我论。在此基础上,列维纳斯提出了他者伦理学——一种尊重他异性,他者优先,对他者负有责任的伦理观。
追根溯源,上帝杀手尼采,杀死上帝的同时,亦杀死了他者——在上帝死亡的瞬间,分崩离析的信仰碎片,弥散进每一个追求个性的主体之中,人人想彰显自我,想成为独在的微型上帝。因此自我无限膨胀,不但将他者同化为同者,还将他者的他异性压缩为微粒,于是一个原子化的轻浮世界诞生了,于是大量书写社会现状的诗歌,亦沦落为轻浅之物。
诗人与时代
我们可以看出,在我们的时代,诗人与民众的关系并不融洽,反而常常剑拔弩张。那么,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:诗人与时代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?他是时代的情侣?还是时代的旁观者?亦或是时代的同时代人?
时代的情侣,热衷于讴歌时代,赞美时代,在时代的森林里夜莺一般婉转鸣唱着他的颂歌。时代的旁观者,则疏离于时代,他仅仅冷眼旁观着时代发生的一切事件。在我看来,一位优秀的现代诗人,应该是我们所处时代的“同时代人”。我这里所言的“同时代人”,并非时代的同路人,而是来自阿甘本哲学语义上的“同时代人”。
法国哲学家罗兰·巴特言“同时代人就是不合时宜的人。”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在巴特的基础上,完善了“同时代人”一词的涵义:1.同时代人是紧紧凝视自己时代的人,以便感知时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的人。2.同时代人不仅仅是指那些感知当下黑暗、领会那注定无法抵达之光的人,同时也是划分和植入时间、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与其他时间联系起来的人。综上所述,一个阿甘本哲学意义上的同时代人,应该具有以下三大特点:1.一个不合时宜的人。2.一个感知时代黑暗的人。3.一个试图改变时代的人。也就是说,这样的人,既不融入时代,也不远离时代,而是处于时代的断裂点上。他紧紧地凝视着时代的黑暗,并有能力在这个断裂点上,植入过去之光,并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当下。
阿甘本“同时代人”的概念,或许不好理解。但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文学史上那些星群般闪烁的显赫姓氏,便会对这一概念有所了解。波德莱尔、卡夫卡、曼德尔施塔姆、鲁迅,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同时代人。若无这些人的存在,他们的时代将在历史的长河里黯淡无光,他们的时代也将变得失聪喑哑。波德莱尔,这位欧美现代诗歌的先驱,就是十九世纪的同时代人。他以一己之力,改变了他所处时代最终的文学走向。
但就是这样一位现代诗歌的奠基人,却是他所处时代的罪人:他的诗作被告上法庭,他的诗集被官方封禁。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期,典雅清丽的浪漫主义诗歌是法国诗坛的主流声音。波德莱尔,这位时代的逆子,却处处与浪漫主义反其道而行之:浪漫主义在诗歌里歌颂大自然的田园风光,波德莱尔则在诗歌里吟咏现代大都市的阴暗角落。浪漫主义诗歌里游走的是贵妇、淑女、绅士,波德莱尔的诗歌里穿行的却是妓女、醉鬼、赌徒。如果说浪漫主义诗人是当时文学界的天使,波德莱尔则是横空出世的撒旦。本雅明曾在评论波德莱尔时言:“诗人们在他们的街道上找到了社会渣滓,并从这种渣滓中繁衍出他们的英雄主人公。”是的,这位文学撒旦,本质上是一位文化英雄。他既叛逆时代,又观察时代。他以一己之力释放了诗歌的新潜能——现代诗歌就此闯入了古典诗歌不能进入的禁忌之区。他紧紧凝视时代之暗的双眼,让他歌咏他所看到的一切:垃圾堆、腐尸、妓院、赌场。他撕开繁华的现代大城市被遮蔽的一角。他的诗歌里,普通民众的身影不停地穿梭。正是从波德莱尔起,确定了现代诗歌的基本调性——现代诗歌是自我与他者共在的诗歌,而非象牙塔里矫揉造作地虚假吟哦。
诗人与民众
一个看重自己使命的诗人,不可能藐视民众。因为他便是民众的一员,他使用与民众相同的语言,他的个人经验里浓缩着民众的集体经验。他与民众不但处于人类命运的共同体,还处于语言的共同体——他是他们的声音,他们通过他来发声。布罗茨基因此写道:“人民性不是政治正确与简单的审美。阿赫玛托娃意识到自己的天职——她的声音是一亿人民的呐喊。”
那些藐视民众,表面上叛逆一切实际上什么也不叛逆的诗人,并非我们的同时代人,反而是被时代潮流席卷而去的人。他们是尤奈斯库荒诞剧里的“犀牛”,也是艾略特诗歌里的空心人。他们穿着现代性礼服,却不知现代性是何物,更不知现代诗是何物,语言是何物。他们的表演性人格,让他们成为一种类似诗人-演员的角色,而非大写的传达民众集体经验的诗人,他们只知道潮流来了,他们得赶快站在潮流之上,乘风破浪,斩获名声。他们是时代之潮可悲的殉葬品。一如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,这乌托邦颂歌队的最佳领唱,当他意识到他所赞美的事物,反过来对他施行思想挤压,他抢先用一粒子弹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——这是他最美的诗行。因为这是一位诗人,用自己的行动与鲜血,怒气冲天地书写着最后的忏悔与反抗。
阿赫玛托娃、曼德尔施塔姆这样的诗人,才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同时代人。正是因为他们,他们所处的时代,才不至于笼罩着无底的黑暗。正是因为他们,后来者才能从历史的废墟里,看到人之为人的尊严。正是因为他们,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声音才会被后世所听见。很多诗评家评论布罗茨基的名作《黑马》时,认为这首诗里的“黑马”意象指的是诗人自己。在我看来,恰恰相反,布罗茨基诗歌里的“黑马”,指的不是他自己,而是他无法逃脱却必须紧紧凝视的他所处的时代:
如此漆黑,黑到了顶点。
如此漆黑,仿佛处于针的内部。
如此漆黑,就像子夜的黑暗。
如此漆黑,如同它前方的树木。
写这首诗的布罗茨基深深意识到,“在我们中间停留”的迟迟不肯离去的时代,正在寻找它的骑手。时代已至,“骑手”何在?“骑手”又是谁?是大写的诗人,是真正的歌者,是在黑马的背上缔造现代诗歌的命运共同体的人。
我们的时代也在呼唤它的同时代人,也在寻找它的骑手。我们时代那个骑在黑马的背上缔造现代诗歌命运共同体的人,他出现了吗?他发声了吗?他已经上路了吗?我不知道。或许他正在扬鞭策马奔驰而来,一如清晨扑面而来的万道光芒。
(原载《草堂》2022年第10卷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