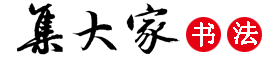总是天已大明
总是天已大明
上一句:
且不可造次
下一句:
就是船上有人追着
原文及意思:
《卷二十七》
诗曰:
夫妻本是同林鸟,大限来时各自飞。
若是遗珠还合浦,却教拂拭更生辉。
话说宋朝汴梁有个王从事,同了夫人到临安调官,赁一民房。居住数日,嫌他窄小不便。王公自到大街坊上寻得一所宅子,宽敞洁净,甚是象意,当把房钱赁下了。归来与夫人说:“房子甚是好住,我明日先搬东西去了,临完,我雇轿来接你。”次日并叠箱笼,结束齐备,王公押了行李先去收拾。临出门,又对夫人道:“你在此等等,轿到便来就是。”王公分付罢,到新居安顿了。就叫一乘轿到旧寓接夫人。轿已去久,竟不见到。王公等得心焦,重到旧寓来问。旧寓人道:“官人去不多时,就有一乘轿来接夫人,夫人已上轿去了。后边又是一乘轿来接,我问他:‘夫人已有轿去了。’那两个就打了空轿回去,怎么还未到?”王公大惊,转到新寓来看。只见两个轿夫来讨钱道:“我等打轿去接夫人,夫人已先来了。我等虽不抬得,却要赁轿钱与脚步钱。”王公道:“我叫的是你们的轿,如何又有甚人的轿先去接着?而今竟不知抬向那里去了。”轿夫道:“这个我们却不知道。”王公将就拿几十钱打发了去,心下好生无主,暴躁如雷,没个出豁处。
次日到临安府进了状,拿得旧主人来,只如昨说,并无异词。问他邻舍,多见是上轿去的。又拿后边两个轿夫来问,说道:“只打得空轿往回一番,地方街上人多看见的,并不知余情。”临安府也没奈何,只得行个缉捕文书,访拿先前的两个轿夫。却又不知姓名住址,有影无踪,海中捞月,眼见得一个夫人送在别处去了。王公凄凄惶惶,苦痛不已。自此失了夫人,也不再娶。
五年之后,选了衢州教授。衢州首县是西安县附郭的,那县宰与王教授时相往来。县宰请王教授衙中饮酒,吃到中间,嘎饭中拿出鳖来。王教授吃了两著,便停了著,哽哽咽咽眼泪如珠,落将下来。县宰惊问缘故。王教授道:“此味颇似亡妻所烹调,故此伤感。”县宰道:“尊阃夫人,几时亡故?”王教授道:“索性亡故,也是天命。只因在临安移寓,相约命轿相接,不知是甚好人,先把轿来骗,拙妻错认是家里轿,上的去了。当时告了状,至今未有下落。”县宰色变了道:“小弟的小妾,正是在临安用三十万钱娶的外方人。适才叫他治庖,这鳖是他烹煮的。其中有些怪异了。”登时起身,进来问妾道:“你是外方人,如何却在临安嫁得在此?”妾垂泪道:“妾身自有丈夫,被好人赚来卖了,恐怕出丈夫的丑,故此不敢声言。”县宰问道:“丈夫何姓?”妾道:“姓王名某,是临安听调的从事官。”县宰大惊失色,走出对王教授道:“略请先生移步到里边,有一个人要奉见。”王教授随了进去。县宰声唤处,只见一个妇人走将出来。教授一认,正是失去的夫人。两下抱头大哭。王教授问道:“你何得在此?”夫人道:“你那夜晚间说话时,民居浅陋,想当夜就有人听得把轿相接的说话。只见你去不多时,就有轿来接。我只道是你差来的,即便收拾上轿去。却不知把我抬到一个甚么去处,乃是一个空房。有三两个妇女在内,一同锁闭了一夜。明日把我卖在官船上了。明知被赚,我恐怕你是调官的人,说出真情,添你羞耻,只得含羞忍耐,直至今日。不期在此相会。”那县官好生过意不去,传出外厢,忙唤值日轿夫将夫人送到王教授衙里。王教授要赔还三十万原身钱,县宰道:“以同官之妻为妾,不曾察听得备细。恕不罪责,勾了。还敢说原钱耶?”教授称谢而归,夫妻欢会,感激县宰不尽。
元来临安的光棍,欺王公远方人,是夜听得了说话,即起谋心,拐他卖到官船上。又是到任去的,他州外府,道是再无有撞着的事了。谁知恰恰选在衢州,以致夫妻两个失散了五年,重得在他方相会。也是天缘未断,故得如此。却有一件:破镜重圆,离而复合,因是好事,这美中有不足处:那王夫人虽是所遭不幸,却与人为妾,已失了身,又不曾查得奸人跟脚出,报得冤仇。不如《崔俊臣芙蓉屏》故事,又全了节操,又报了冤仇,又重会了夫妻。这个话好听。看官,容小子慢慢敷演,先听《芙蓉屏歌》一篇,略见大意。歌云:
画芙蓉,妾忍题屏风,屏间血泪如花红。败叶枯梢两萧索,断嫌遗墨俱零落。去水奔流隔死生,孤身只影成漂泊。成漂泊,残骸向谁托?泉下游魂竟不归,图中艳姿浑似昨。浑似昨,妾心伤,那禁秋雨复秋霜!宁肯江湖逐舟子,甘从宝地礼医王。医王本慈悯,慈悯超群品。逝魄愿提撕,节嫠赖将引。芙蓉颜色娇,夫婿手亲描。花萎因折蒂,干死为伤苗。蕊干心尚苦,根朽恨难消!但道章台泣韩翎,岂期甲帐遇文萧?芙蓉良有意,芙蓉不可弃。享得宝月再团圆,相亲相爱莫相捐!谁能听我芙蓉篇?人间夫妇休反目,看此芙蓉真可怜!
这篇歌,是元朝至正年间真州才土陆仲旸所作。你道他为何作此歌?只因当时本州有个官人,姓崔名英,字俊臣,家道富厚,自幼聪明,写字作画,工绝一时。娶妻王氏,少年美貌,读书识字,写染皆通。夫妻两个真是才子佳人,一双两好,无不厮称,恩爱异常。是年辛卯,俊臣以父荫得官,补浙江温州永嘉县尉,同妻赴任。就在真州闸边,有一只苏州大船,惯走杭州路的,船家姓顾。赁定了,下了行李,带了家奴使婢,由长江一路进发,包送到杭州交卸。行到苏州地方,船家道:“告官人得知,来此已是家门首了。求官人赏赐些,并买些福物纸钱,赛赛江湖之神。”俊臣依言,拿出些钱钞,教如法置办。完事毕,船家送一桌牲酒到舱里来。俊臣叫人家接了,摆在桌上同王氏暖酒少酌。俊臣是宦家子弟,不懂得江湖上的禁忌。吃酒高兴,把箱中带来的金银杯觥之类,拿出与王氏欢酌。却被船家后舱头张见了,就起不良之心。
此时七月天气,船家对官舱里道:“官人,娘子在此闹处歇船,恐怕热闷。我们移船到清凉些的所在泊去,何如?”俊臣对王氏道:“我们船中闷躁得不耐烦,如此最好。”王氏道:“不知晚间谨慎否?”俊臣道:“此处须是内地,不比外江。况船家是此间人,必知利害,何妨得呢?”就依船家之言,凭他移船。那苏州左近太湖,有的是大河大洋。官塘路上,还有不测;若是傍港中去,多是贼的家里。俊臣是江北人,只晓得扬子江有强盗,道是内地港道小了,境界不同,岂知这些就里?是夜船家直把船放到芦苇之中,泊定了。黄昏左侧,提了刀,竟奔舱里来。先把一个家人杀了,俊臣夫妻见不是头,磕头讨饶道:“是有的东西,都拿了去,只求饶命!”船家道:“东西也要,命也要。”两个只是磕斗,船家把刀指着王氏道:“你不必慌,我不杀你,其余都饶不得。”俊臣自知不免,再三哀求道:“可怜我是个书生,只教我全尸而死罢。”船家道:“这等饶你一刀,快跳在水中去!”也不等俊臣从容,提着腰胯,扑通的掩下水去。其余家僮、使女尽行杀尽,只留得王氏一个。对王氏道:“你晓得免死的缘故么?我第二个儿子,未曾娶得媳妇,今替人撑船到杭州去了。再是一两个月,才得归来,就与你成亲。你是吾一家人了,你只安心住着,自有好处,不要惊怕。”一头说,一头就把船中所有,尽检点收拾过了。
王氏起初怕他来相逼,也拚一死。听见他说了这些话,心中略放宽些道:“且到日后再处。”果然此船家只叫王氏做媳妇,王氏假意也就应承。凡是船家教他做些什么,他千依百顺.替他收拾零碎,料理事务,真象个掌家的媳妇伏侍公公一般,无不任在身上,是件停当。船家道:“是寻得个好媳妇。”真心相待,看看熟分,并不提防他有外心了。
如此一月有余,乃是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令。船家会聚了合船亲属、水手人等,叫王氏治办酒者,盛设在舱中饮酒看月。个个吃得酩酊大醉,东倒西歪,船家也在船里宿了。王氏自在船尾,听得鼾睡之声彻耳,于时月光明亮如昼,仔细看看舱里,没有一个不睡沉了。王氏想道:“此时不走,更待何时?”喜得船尾贴岸泊着,略摆动一些些就好上岸。王氏轻身跳了起来,趁着月色,一气走了二三里路。走到一个去处,比旧路绝然不同。四望尽是水乡,只有芦苇菰蒲,一望无际。仔细认去,芦苇中间有一条小小路径,草深泥滑,且又双弯纤细,鞋弓袜小,一步一跌,吃了万千苦楚。又恐怕后边追来,不敢停脚,尽力奔走。
渐渐东方亮了,略略胆大了些。遥望林木之中,有屋宇露出来。王氏道:“好了,有人家了。”急急走去,到得面前,抬头一看,却是一个庵院的模样,门还关着。王氏欲待叩门,心里想道:“这里头不知是男僧女僧,万一敲开门来,是男僧,撞着不学好的,非礼相犯,不是才脱天罗,又罹地网?且不可造次。总是天已大明,就是船上有人追着,此处有了地方,可以叫喊求救,须不怕他了。只在门首坐坐,等他开出来的是。”须臾之间,只听得里头托的门栓晌处,开将出来,乃是一个女僮,出门担水。王氏心中喜道:“元来是个尼庵。”一径的走将进去。院主出来见了,问道:“女娘是何处来的?大清早到小院中。”王氏对蓦生人,未知好歹,不敢把真话说出来,哄他道:“妾是真州人,乃是永幕崔县尉次妻,大娘子凶悍异常,万般打骂。近日家主离任归家,泊舟在此。昨夜中秋赏月,叫妾取金杯饮酒,不料偶然失手,落到河里去了。大娘子大怒,发愿必要置妾死地。妾自想料无活理,乘他睡熟,逃出至此。”院主道:“如此说来,娘子不敢归舟去了。家乡又远,若要别求匹偶,一时也未有其人。孤苦一身,何处安顿是好?”王氏只是哭泣不止。
院主见他举止端重,情状凄惨,好生慈悯,有心要收留他。便道:“老尼有一言相劝,未知尊意若何?”王氏道:“妾身患难之中,若是师父有甚么处法,妾身敢不依随?”院主道:“此间小院,僻在荒滨,人迹不到,茭葑为邻,鸥鹭为友,最是个幽静之处。幸得一二同伴,都是五十以上之人。侍者几个,又皆淳谨。老身在此往迹,甚觉清修味长。娘子虽然年芳貌美,争奈命蹇时乖,何不舍离爱欲,披缁削发,就此出家?禅榻佛灯,晨飨暮粥,且随缘度其日月,岂不强如做人婢妾,受今世的苦恼,结来世的冤家么?”王氏听说罢,拜谢道:“师父若肯收留做弟子,便是妾身的有结果了。还要怎的?就请师父替弟子落了发,不必迟疑。”果然院主装起香,敲起磬来,拜了佛,就替他落了发:
可怜县尉孺人,忽作如来弟子。
落发后,院主起个法名,叫做慧圆,参拜了三宝。就拜院主做了师父,与同伴都相见已毕,从此在尼院中住下了。王氏是大家出身,性地聪明。一月之内,把经典之类,一一历过,尽皆通晓。院主大相敬重,又见他知识事体,凡院中大小事务,悉凭他主张。不问过他,一件事也不敢轻做。且是宽和柔善,一院中的人没一个不替他相好,说得来的。每日早晨,在白衣大土前礼拜百来拜,密诉心事。任是大寒大暑,再不间断。拜完,只在自己静室中清坐。自怕貌美,惹出事来,再不轻易露形,外人也难得见他面的。
如是一年有余。忽一日,有两个人到院随喜,乃是院主认识的近地施主,留他吃了些斋。这两个人是偶然闲步来的,身边不曾带得甚么东西来回答。明日将一幅纸画的芙蓉来,施在院中张挂,以答谢昨日之斋。院主受了,便把来裱在一格素屏上面。王氏见了,仔细认了一认,问院主道:“此幅画是那里来的?”院主道:“方才檀越布施的。”王氏道。“这檀越是何姓名?住居何处?”院土道:“就是同县顾阿秀兄弟两个。”王氏道:“做甚么生理的?”院主道:“他两个原是个船户,在江湖上赁载营生。近年忽然家事从容了,有人道他劫掠了客商,以致如此。未知真否如何。”王氏道:“长到这里来的么?”院主道:“偶然来来,也不长到。”
王氏问得明白,记了顾阿秀的姓名,就提笔来写一首词在屏上。词云:
少日风流张敞笔,写生不数今黄筌。芙蓉画出最鲜妍。岂知娇艳色,翻抱死生缘?粉绘凄凉余幻质,只今流落有谁怜?素屏寂寞伴枯禅。今生缘已断,愿结再生缘!——右调《临江仙》。
院中之尼,虽是识得经典上的字,文义不十分精通。看见此词,只道是王氏卖弄才情,偶然题咏,不晓中间缘故。谁知这回来历,却是崔县尉自己手笔画的,也是船中劫去之物。王氏看见物在人亡,心内暗暗伤悲。又晓得强盗踪迹,已有影响,只可惜是个女身,又已做了出家人,一时无处申理。忍在心中,再看机会。
却是冤仇当雪,姻缘未断,自然生出事体来。
姑苏城里有一个人,名唤郭庆春,家道殷富,最肯结识官员土夫。心中喜好的是文房清玩。一日游到院中来,见了这幅芙蓉画得好,又见上有题咏,字法俊逸可观,心里喜欢不胜。问院主要买,院主与王氏商量,王氏自忖道:“此是丈夫遗迹,本不忍舍;却有我的题词在上,中含冤仇意思在里面,遇着有心人玩着词句,究问根由,未必不查出踪迹来。若只留在院中,有何益处?”就叫:“师父卖与他罢。”庆春买得,千欢万喜去了。
其时有个御史大夫高公,名纳麟,退居姑苏,最喜欢书画。郭庆春想要奉承他,故此出价钱买了这幅纸屏去献与他。高公看见画得精致,收了他的,忙忙里也未看着题词,也不查着款字,交与书,分付且张在内书房中,送庆春出门来别了。只见外面一个人,手里拿着草书四幅,插个标儿要卖。高公心性既爱这行物事,眼里看见,就不肯便放过了,叫取过来看。那人双手捧递,高公接上手一看:
字格类怀素,清劲不染俗。
芳列法书中,可栽《金石录》。
高公看毕,道:“字法颇佳,是谁所写?”那人答道:“是某自己学写的。”高公抬起头来看他,只见一表非俗,不觉失惊。问道:“你姓甚名谁?何处人氏?”那个人吊下泪来道:“某姓崔名英,字俊臣,世居真州。以父荫补永幕县尉,带了家眷同往赴任,自不小心,为船人所算,将英沉于水中。家财妻小,都不知怎么样了?幸得生长江边,幼时学得泅水之法,伏在水底下多时,量他去得远了,然后爬上岸来,投一民家。浑身沾湿,并无一钱在身。赖得这家主人良善,将干衣出来换了,待了酒饭,过了一夜。明日又赠盘缠少许,打发道:‘既遭盗劫,理合告官。恐怕连累,不敢奉留。’英便问路进城,陈告在平江路案下了。只为无钱使用,缉捕人役不十分上紧。今听侯一年,杳无消耗。无计可奈,只得写两幅字卖来度日。乃是不得已之计,非敢自道善书,不意恶札,上达钧览。”
高公见他说罢,晓得是衣冠中人,遭盗流落,深相怜悯。又见他字法精好,仪度雍容,便有心看顾他。对他道:“足下既然如此,目下只索付之无奈,且留吾西塾,教我诸孙写字,再作道理。意下如何?”崔俊臣欣然道:“患难之中,无门可投。得明公提携,万千之幸!”高公大喜,延入内书房中,即治酒相待。正欢饮间,忽然抬起头来,恰好前日所受芙蓉屏,正张在那里。俊臣一眼瞟去见了,不觉泫然垂泪。高公惊问道:“足下见此芙蓉,何故伤心?”俊臣道:“不敢欺明公,此画亦是舟中所失物件之一,即是英自己手笔。只不知何得在此。”站起身来再者看,只见有一词。俊臣读罢,又叹息道:“一发古怪!此词又即是英妻王氏所作。”高公道:“怎么晓得?”俊臣道:“那笔迹从来认得,且词中意思有在,真是拙妻所作无疑。但此词是遭变后所题,拙妇想是未曾伤命,还在贼处。明公推究此画来自何方,便有个根据了。”高公笑道:“此画来处有因,当为足下任捕盗之责,且不可泄漏!”是日酒散,叫两个孙子出来拜了先生,就留在书房中住下了。自此俊臣只在高公门馆,不题。
却说高公明日密地叫当直的请将郭庆春来,问道:“前日所惠芙蓉屏,是那里得来的?”庆春道:“卖自城外尼院。”高公问了去处,别了庆春,就差当直的到尼院中仔细盘问:“这芙蓉屏是那里来的?又是那个题咏的?”王氏见来问得蹊跷,就叫院主转问道:“来问的是何处人?为何问起这些缘故?”当直的回言:“这画而今已在高府中,差来问取来历。”王氏晓得是官府门中来问,或者有些机会在内,叫院主把真话答他道:“此画是同县顾阿秀舍的,就是院中小尼慧圆题的。”当直的把此言回复高公。高公心下道:“只须赚得慧圆到来,此事便有着落。”进去与夫人商议定了。
隔了两日,又差一个当直的,分付两个轿夫抬了一乘轿到尼院中来。当直的对院主道:“在下是高府的管家。本府夫人喜诵佛经,无人作伴。闻知贵院中小师慧圆了悟,愿礼请拜为师父,供养在府中。不可推却!”院主迟疑道:“院中事务大小都要他主张,如何接去得?”王氏闻得高府中接他,他心中怀着复仇之意,正要到官府门中走走,寻出机会来。亦且前日来盘问芙蓉屏的,说是高府,一发有些疑心。便对院主道:“贵宅门中礼请,岂可不去?万一推托了,惹出事端来,怎生当抵?”院主晓得王氏是有见识的,不敢违他,但只是道:“去便去,只不知几时可来。院中有事怎么处?”王氏道:“等见夫人过,住了几日,觑个空便,可以来得就来。想院中也没甚事,倘有疑难的,高府在城不远,可以来问信商量得的。”院主道:“既如此,只索就去。”当直的叫轿夫打轿进院,王氏上了轿,一直的抬到高府中来。
高公未与他相见,只叫他到夫人处见了,就叫夫人留他在卧房中同寝,高公自到别房宿歇。夫人与他讲些经典,说些因果,王氏问一答十,说得夫人十分喜欢敬重。闲中间道:“听小师父一谈,不是这里本处人。还是自幼出家的?还是有过丈夫,半路出家的?”王氏听说罢,泪如雨下道:“复夫人:小尼果然不是此间,是真州人。丈夫是永幕县尉,姓崔名英,一向不曾敢把实话对人说,而今在夫人面前,只索实告,想自无妨。”随把赴任到此,舟人盗劫财物,害了丈夫全家,自己留得性命,脱身逃走,幸遇尼僧留住,落发出家的说话,从头至尾,说了一遍,哭泣不止。
夫人听他说得伤心,恨恨地道:“这些强盗,害得人如此!天理昭彰,怎不报应?”王氏道:“小尼躲在院中一年,不见外边有些消耗。前日忽然有个人拿一幅画芙蓉到院中来施。小尼看来,却是丈夫船中之物。即向院主问施人的姓名,道是同县顾阿秀兄弟。小尼记起丈夫赁的船正是船户顾姓的。而今真赃已露,这强盗不是顾阿秀是谁?小尼当时就把舟中失散的意思,做一首词,题在上面。后来被人买去了。贵府有人来院,查问题咏芙蓉下落。其实即是小尼所题,有此冤情在内。”即拜夫人一拜道:“强盗只在左近,不在远处了。只求夫人转告相公,替小尼一查。若是得了罪人,雪了冤仇,以下报亡夫,相公、夫人恩同天地了!”夫人道:“既有了这些影迹,事不难查,且自宽心!等我与相公说就是。”
夫人果然把这些备细,一一与高公说了。又道:“这人且是读书识字,心性贞淑,决不是小家之女。”高公道:“听他这些说话与崔县尉所说正同。又且芙蓉屏是他所题,崔县尉又认得是妻子笔迹。此是崔县尉之妻,无可疑心。夫人只是好好看待他,且不要说破。”高公出来见崔俊臣时,俊臣也屡屡催高公替他查查芙蓉屏的踪迹。高公只推未得其详,略不提起慧圆的事。
高公又密密差人问出顾阿秀兄弟居址所在,平日出没行径,晓得强盗是真。却是居乡的官,未敢轻自动手。私下对夫人道:“崔县尉事,查得十有七八了,不久当使他夫妻团圆。但只是慧圆还是个削发尼僧,他日如何相见,好去做孺人?你须慢慢劝他长发改妆才好。”夫人道:“这是正理。只是他心里不知道丈夫还在,如何肯长发改妆?”高公道:“你自去劝他,或者肯依因好;毕竟不肯时节,我另自有说话。”夫人依言,来对王氏道:“吾已把你所言尽与相公说知,相公道:‘捕盗的事,多在他身上,管取与你报冤。’”王氏稽首称谢。夫人道:“只有一件:相公道,你是名门出身,仕宦之妻,岂可留在空门没个下落?叫我劝你长发改妆。你若依得,一力与你擒盗便是。”王氏道:“小尼是个未亡之人,长发改妆何用?只为冤恨未伸,故此上求相公做主。若得强盗歼灭,只此空门静守,便了终身。还要甚么下落?”夫人道:“你如此妆饰,在我府中也不为便。不若你留了发,认义我老夫妇两个,做个孀居寡女,相伴终身。未为不可。”王氏道:“承家相公,夫人抬举,人非木石,岂不知感?但重整云鬟,再施铅粉,丈夫已亡,有何心绪?况老尼相救深恩,一旦弃之,亦非厚道。所以不敢从命。”夫人见他说话坚决,一一回报了高公。高公称叹道:“难得这样立志的女人!”又叫夫人对他说道:“不是相公苦苦要你留头,其间有个缘故。前日因去查问此事,有平江路官吏相见,说:‘旧年曾有人告理,也说是永幕县尉,只怕崔生还未必死。’若是不长得发,他日一时擒住此盗,查得崔生出来,此时僧俗各异,不得团圆,悔之何及!何不权且留了头发?等事体尽完,崔生终无下落,那时任凭再净了发,还归尼院,有何妨碍?”王氏见说是有人还在此告状,心里也疑道:“丈夫从小会没水,是夜眼见得囫囵抛在水中的,或者天幸留得性命也不可知。”遂依了夫人的话,虽不就改妆,却从此不剃发,权扮作道站模样了。
又过了半年,朝廷差个进土薛缚化为监察御史,来按平江路。这个薛御史乃是高公旧日属官,他吏才精敏,是个有手段的。到了任所,先来拜谒高公。高公把这件事密密托他,连顾阿秀姓名、住址、去处,都细细说明白了。薛御史谨记在心,自去行事,不在话下。
且说顾阿秀兄弟,自从那年八月十五夜一觉直睡到天明,醒来不见了王氏,明知逃去,恐怕形迹败露,不敢明明追寻。虽在左近打听两番,并无踪影,这是不好告诉人的事,只得隐忍罢了。此后一年之中,也曾做个十来番道路,虽不能如崔家之多,侥幸再不败露,甚是得意。一日正在家欢呼饮酒间,只见平江路捕盗官带者一哨官兵,将宅居围住,拿出监察御史发下的访单来。顾阿秀是头一名强盗,其余许多名字,逐名查去,不曾走了一个。又拿出崔县尉告的赃单来,连他家里箱笼,悉行搜卷,并盗船一只,即停泊门外港内,尽数起到了官,解送御史衙门。
薛御史当堂一问,初时抵赖;及查物件,见了永幕县尉的敕牒尚在箱中,赃物一一对款,薛御史把崔县尉旧日所告失盗状,念与他听,方各俯首无词。薛御史问道:“当日还有孺人王氏,今在何处?”顾阿秀等相顾不出一语。御史喝令严刑拷讯。顾阿秀招道:“初意实要留他配小的次男,故此不杀。因他一口应承,愿做新妇,所以再不防备。不期当年八月中秋,乘睡熟逃去,不知所向。只此是实情。”御史录了口词,取了供案,凡是在船之人,无分首从,尽问成枭斩死罪,决不待时。原赃照单给还失主。御史差人回复高公,就把赃物送到高公家来,交与崔县尉。俊臣出来,一一收了。晓得敕牒还在,家物犹存,只有妻子没查下落处,连强盗肚里也不知去向了,真个是渺茫的事。俊臣感新思旧,不觉励哭起来。有诗为证:
堪笑聪明崔俊臣,也应落难一时浑。
既然因画能追盗,何不寻他题画人?
元来高公有心,只将画是顾阿秀施在尼院的说与俊臣知道,并不曾提起题画的人,就在院中为尼,所以俊臣但得知盗情,因画败露,妻子却无查处,竟不知只在画上,可以跟寻出来的。
当时俊臣励哭已罢,想道:“既有敕牒,还可赴任。若再稽迟,便恐另补有人,到不得地方了。妻子既不见,留连于此无益。”请高公出来拜谢了,他就把要去赴任的意思说了。高公道:“赴任是美事,但足下青年无偶,岂可独去?待老夫与足下做个媒人,娶了一房孺人,然后夫妻同往也未为迟。”俊臣含泪答道:“糟糠之妻,同居贫贱多时,今遭此大难,流落他方,存亡未卜。然据者芙蓉屏上尚及题词,料然还在此方。今欲留此寻访,恐事体渺茫,稽迟岁月,到任不得了。愚意且单身到彼,差人来高揭榜文,四处追探,拙妇是认得字的。传将开去,他闻得了,必能自出。除非忧疑惊恐,不在世上了。万一天地垂怜,尚然留在,还指望伉俪重谐。英感明公恩德,虽死不忘,若别娶之言,非所愿闻。”高公听他说得可怜,晓得他别无异心,也自凄然道:“足下高谊如此,天意必然相佑,终有完全之日。吾安敢强逼?只是相与这几时,容老夫少尽薄设奉饯,然后起程。”
次日开宴饯行,邀请郡中门生、故吏、各官与一时名土毕集,俱来奉陪崔县尉。酒过数巡,高公举杯告众人道:“老夫今日为崔县尉了今生缘。”众人都不晓其意,连崔俊臣也一时未解,只见高公命传呼后堂:“请夫人打发慧圆出来!”俊臣惊得目呆,只道高公要把甚么女人强他纳娶,故设此宴,说此话,也有些着急了。梦里也不晓得他妻子叫得甚么慧圆!当时夫人已知高公意思,把崔县尉在馆内多时,昨已获了强盗,问了罪名,追出敕牒,今日饯行赴任,特请你到堂厮认团圆,逐项逐节的事情,说了一遍。王氏如梦方醒,不胜感激。先谢了夫人,走出堂前来,此时王氏发已半长,照旧妆饰。崔县尉一见,乃是自家妻子,惊得如醉里梦里。高公笑道:“老夫原说道与足下为媒,这可做得着么?”崔县尉与王氏相持大恸,说道:“自料今生死别了,谁知在此,却得相见?”
座客见此光景,尽有不晓得详悉的,向高公请问根由。高公便叫书僮去书房里取出芙蓉屏来,对众人道:“列位要知此事,须看此屏。”众人争先来看,却是一国一题。看的看,念的念,却不明白这个缘故。高公道:“好教列位得知,只这幅画,便是崔县尉夫妻一段大姻缘。这回即是崔县尉所画,这词即是崔孺人所题。他夫妻赴任到此,为船上所劫。崔孺人脱逃于尼院出家,遇人来施此画,认出是船中之物,故题此词。后来此画却入老夫之手。遇着崔县尉到来,又认出是孺人之笔。老夫暗地着人细细问出根由,乃知孺人在尼院,叫老妻接将家来往着。密行访缉,备得大盗踪迹。托了薛御史究出此事,强盗俱已伏罪。崔县尉与孺人在家下,各有半年多,只道失散在那里,竟不知同在一处多时了。老夫一向隐忍,不通他两人知道,只为崔孺人头发未长,崔县尉敕牒未获,不知事体如何,两心事如何?不欲造次漏泄。今罪人既得,试他义夫节妇,两下心坚,今日特地与他团圆这段因缘,故此方才说替他了今生缘,即是崔孺人词中之句,方才说。‘请慧圆’,乃是崔孺人尼院中所改之字,特地使崔君与诸公不解,为今日酒间一笑耳。”崔俊臣与王氏听罢,两个哭拜高公,连在坐之人无不下泪,称叹高公盛德,古今罕有。王氏自到里面去拜谢夫人了。高公重入座席,与众客尽欢而散。是夜特开别院,叫两个养娘付侍王氏与崔县尉在内安歇。
明日,高公晓得崔俊臣没人伏侍,赠他一奴一婢,又赠他好些盘缠,当日就道。他夫妻两个感念厚恩,不忍分别,大哭而行。王氏又同丈夫到尼院中来,院主及一院之人,见他许久不来,忽又改妆,个个惊异。王氏备细说了遇合缘故,并谢院主看待厚意。院主方才晓得顾阿秀劫掠是真,前日王氏所言妻妾不相容,乃是一时掩饰之词。院中人个个与他相好的,多不舍得他去。事出无奈,各各含泪而别。夫妻两个同到永嘉去了。
在永嘉任满回来,重过苏州,差人问侯高公,要进来拜谒。谁知高公与夫人俱已薨逝,殡葬已毕了。崔俊臣同王氏大哭,如丧了亲生父母一般。问到他墓下,拜奠了,就请旧日尼院中各众,在墓前建起水陆道场,三昼夜,以报大恩。王氏还不忘经典,自家也在里头持诵。事毕,同众尼再到院中。崔俊臣出宦资,厚赠了院主。王氏又念昔日朝夜祷祈观世音暗中保佑,幸得如愿,夫妇重谐,出白金十两,留在院主处,为烧香点烛之费。不忍忘院中光景,立心自此长斋念观音不辍,以终其身。当下别过众尼,自到真州字家,另日赴京补官,这是后事,不必再题。
此本话文,高公之德,崔尉之谊,王氏之节,皆是难得的事。各人存了好心,所以天意周全,好人相逢。毕竟冤仇尽报,夫妇重完,此可为世人之劝。诗云:
王氏藏身有远图,间关到底得逢夫。
舟人妄想能同志,一月空将新妇呼。
又诗云:
芙蓉本似美人妆,何意飘零在路旁?
画笔词锋能巧合,相逢犹自墨痕香。
又有一首赞叹御史大夫高公云:
高公德谊薄云天,能结今生未了缘。
不便初时轻逗漏,致今到底得团圆。
芙蓉画出原双蒂,萍藻浮来亦共联。
可惜白杨堪作柱,空教洒泪及黄泉。